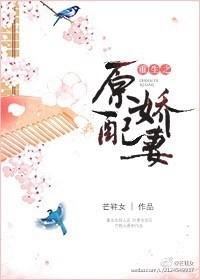69中文网>农家辣娘子 > 第一百二十二章 五娘指引隐玄机(第1页)
第一百二十二章 五娘指引隐玄机(第1页)
夕阳的余晖洒在药斋的门匾上,“济世堂”三个字在暮色中依然清晰可见。孙星站在柜台后,望着眼前这位满脸皱纹、衣着朴素的老妇人,心中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
黄婶紧紧攥着孙子的手,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董神医,求您救救我孙子吧!”她的声音颤抖着,仿佛整个人都在微微抖。
一旁的梁宁看着这熟悉的一幕,不由得暗自叹息。这已经是黄婶第七次来药斋了,每次都是在傍晚人少的时候,带着她那个神志不清的孙子前来求医。
“黄婶,您先别着急。”孙星柔声安抚道,目光落在那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身上。少年一脸茫然,眼神空洞,嘴角挂着些许涎水,活像个不谙世事的幼童。
孙星示意梁宁搬来一张椅子,让少年坐下。她仔细查看着少年的瞳孔反应,又细细把了脉,眉头渐渐皱起。
“黄婶,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孙星柔边诊脉一边问道。
黄婶抹了抹眼角,声音哽咽:“三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得了场大病,高烧,烧得人都迷糊了。等退烧后……就……就成这样了。”
“当时可有请大夫看过?”
“看过,看过好几个大夫。”黄婶急切地说道,“可都说没办法,说是烧坏了脑子。”
梁宁在一旁听得直摇头,这种情况他见得多了。一般的大夫遇到这种病症,大多都是摇头叹气,说什么天命难违。
孙星又仔细检查了少年的四肢反应和语言能力,现他除了偶尔出些含糊不清的音节外,基本无法与人交流。就连最简单的动作,比如拿筷子、系衣扣这些,都无法完成。
“董神医,您就给句准话吧。”黄婶双手紧握,眼中含泪,“我这孙子,还有救吗?”
药斋里一时陷入沉默。陈管事放下手中的账本,也将目光投向孙星。就连门外经过的几个病人也不由得放慢脚步,想听听这位神医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孙星轻轻叹了口气:“黄婶,实话跟您说,孩子的情况确实很严重。高烧伤了脑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黄婶的身子猛地一颤,眼中的光芒瞬间黯淡下来。
“不过……”孙星话锋一转,“虽然完全康复几乎不可能,但通过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或许能改善他现在的状况。”
“真的吗?”黄婶猛地抬起头,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梁宁也是一惊,他跟随孙星学医已有一段时间,深知她从不轻易许诺。既然敢这么说,必定是有几分把握。
“我这里有一套针灸方案,配合一些药物调理,应该能帮助他恢复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孙星说着,已经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效果也不会太明显。”
“只要有希望就好!”黄婶激动得就要跪下,“只要他能自己吃饭穿衣,能知道冷暖,我就知足了!”
孙星连忙扶住她:“黄婶使不得!您先别激动。这是第一副方子,先吃上半个月,然后每三天来一次,我给他施针。”
“好好好!”黄婶连连点头,小心翼翼地接过方子,生怕弄皱了似的。
就在这时,孙星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黄婶,您是怎么知道要来找我的?”
“从五姑娘那儿得知。”黄婶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她说您是神医孙娘子,专门治疗疑难杂症。要不是她指点,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五姑娘?孙星眉头微皱,与梁宁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