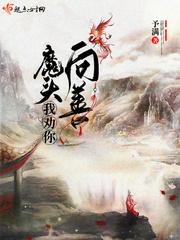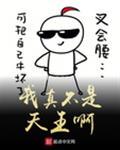69中文网>大秦:献图监国,始皇求我继承大统 > 141章 第一次试考(第1页)
141章 第一次试考(第1页)
“上谷郡的刘主簿,我已经使人递了话,也送了‘程仪’。”一个身着暗纹锦袍的公子压低声音,得意洋洋,“他说卷子左上角若有三点水纹为记,他阅卷时便会‘多加照拂’,至少能过初试。”
“可万一考题与咱们花大价钱从宫里弄出来的那几套‘秘卷’不一样,如何是好?”另一人搓着手,显得有些紧张。
“怕什么!”最初说话的锦袍公子嗤笑一声,“我等只需将那些‘奇文警句’背熟,不管题目为何,只管洋洋洒洒写上去便是。他将闾还能将所有世家子弟都黜落不成?法不责众,他总得给几分薄面!”
监国府,书房内灯火通明。
张洪奎将最新的密报呈上,声音平稳无波:“殿下,赵家、何家等,已按计划‘资助’了近三百名所谓的‘寒门学子’,多是些市井泼皮、游手好闲之徒,或是头脑愚笨之人。他们被那些管事暗中嘱咐,在考场上大放厥词,胡写乱画,甚至可以当场喧哗,以败坏科举声名,证明寒门不堪造就。”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各家子弟也准备了诸多作弊的手段,从衣袖夹带小抄到买通考场书吏传递答案,花样百出。有几人甚至以为买通了此次负责出题的某位博士,已拿到了‘真题’,正日夜背诵。”
将闾放下手中的南疆军务文书,拿起密报随意翻了翻,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带着些许嘲弄的弧度:“他们倒是……迫不及待想登台献丑,生怕错过这场好戏。”
他看向张洪奎,眼神平静:“那些‘善人’的嘴脸,还有他们教唆的过程,可都录下来了?”
“殿下放心,罗网的影石不是摆设,一言一行,一清二楚。他们如何巧言令色地教唆,那些泼皮如何点头哈腰地应承,皆有记录,足以让他们百口莫辩。”
“很好。”将闾点了点头,手指在桌案上轻轻叩击,“传令杜周,各县考场的用度,尤其是笔墨纸张,务必保证足额供应,且要用上等松烟墨、韧皮纸。
莫让那些真正想凭才学一搏的学子,因为这些腌臜伎俩而受了委屈,断了前程。
钱不够,就从那几个被抄的逆党府库里拨。”
杜周前几日还为钱粮之事愁得头发都多白了几根,得了将闾这道密令,又听说经费有了着落。
杜周顿时眉开眼笑,拍着胸脯保证,就算他亲自去监工,也绝不让一分钱被贪墨,一张纸被调换。
将闾又道:“再传令冯劫大人,考场纪律,按原先议定的,从严再从严!卫尉府全力配合,各地郡兵严阵以待,但有喧哗作弊、扰乱考场者,立时拿下,不必请示。‘糊名’、‘誊录’之法,必须务必执行到位,确保阅卷公平公正。”
张洪奎领命。
将闾的目光转向窗外,夜色如墨,星光寥落。
“那些世家以为,他们能操纵人心,玩弄规则,将科举变成一场闹剧。他们错了。”将闾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却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本殿的掌握之中。本殿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游戏规则,由谁来制定。”
“殿下英明。”张洪奎由衷赞叹。他跟随将闾日久,深知这位年轻的监国公子胸有丘壑,算无遗策。
那些世家自以为得计的小聪明,在殿下眼中,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把戏罢了。
几日后,咸阳城外各县,首场县试如期举行。
考场设在各县的学宫或官衙,考棚简陋,却也整洁。
考场外,卫尉府的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气氛肃穆。
前来应试的学子们,鱼贯而入,神情各异。
有胸有成竹、意气风发的世家子弟,也有面色紧张、衣衫褴褛的寒门少年。
赵家、何家等安排的那些“寒门学子”,也夹杂其中,他们大多没读过几天书,对科举一窍不通,只想着完成那些管事交代的任务,便能拿到许诺的赏钱。
考场内,钟声响起,考试正式开始。
那些世家子弟,大多早已胸有成竹,奋笔疾书,将背诵的“锦囊妙计”和准备好的“时政策论”洋洋洒洒地写在试卷上,只盼能一举高中。
而那些被赵家等收买的“寒门学子”,则开始按计划行动。
“这考的是什么玩意儿?老子一个字都看不懂!”一个满脸横肉的少年,抓耳挠腮,对着试卷破口大骂。
“就是!老子还以为能考些吃喝玩乐,没想到全是这些酸不拉几的东西!”另一个少年也跟着起哄。
两人故意提高嗓门,引得周围考生纷纷侧目。
考场上的监考官见状,立刻上前制止:“肃静!考场之上,不得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