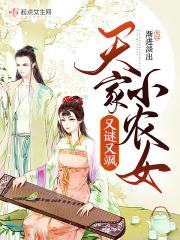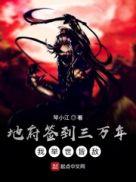69中文网>贵妃失忆之后 > 6070(第10页)
6070(第10页)
沈幼宜垂眸,昭王在朝中有尚书令的官职,执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名义上是六部的最高长官。
太子殿下语气里尽是对弟弟的关怀:“朝事繁琐,许多事你也不必急着上手,多熟悉一番无妨。”
沈幼宜品着太子言下之意,无外乎是昭王虽军功卓著,但于朝堂上欠缺之处还有很多。
科举行贿一案牵连甚广,大有法不责众之意。
谢明霁自顺隆衣铺始,先后清查怡棠楼、天宝当铺等多处据点。
会试考生贿赂主考官,明目繁多。
譬如入当铺,以低价典当珍宝,此为定银。中举后再以高价赎回,一来一回,流水般的银子就神不知鬼不觉进了当铺。又或者,天宝当铺摆出种种赝品,士子当珍品来赎,分三六九等。贿银多少,名次便能大致落在多少。
寻枪手代考亦可。有专人做策应,牵线找到考生中有意旁门左道者,于声色之地洽谈。怡棠楼中,若是点海棠或是桃珠几位姑娘,其实找的便是背后的枪手。
士子间口口相传,盘根错节,彼此又拿捏住舞弊的把柄,无需担心泄密。
如此隐晦行事,得利不知凡几。
枪替夹带于乡试中最甚,多少人借此谋得举人功名。
到了会试之时,且看贿赂主考官的神通。
这十余年先帝厚待文臣,数次开恩科。作奸犯科者除非十恶不赦,量刑一律从宽。如此仁君,却纵沈出朝中一帮奸佞,大胆染指科举。心怀不正的读书人上行下效,与之沆瀣一气。试问他们中第之后,如何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朝廷取士乃国之根本,断不能沈奸邪为祸朝堂,断天下读书人之后路。
新帝御极,正是锐不可当之时,必要一举铲除此祸患。
“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谢明霁次日便要动身往宣平府,彻查元和三十年乡试。
离去之际,他倒还有一处不明。
元朔帝知道他心中所虑,淡淡道:“想问便问罢。”
“是,多谢陛下。”谢明霁开门见山,“不知陛下预备如何处置沈长瑾?”
从江南水患后,平心而论,他再未将沈长瑾与首辅奸党一概而论。
那时江南暴雨倾盆,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朝廷拨粮,层层盘剥。江南官商勾结,哄抬粮价,灾民深受其苦,饿死者不计其数。
赈灾队伍中尚有陈党官员掣肘,官官相护,又刻意引灾民暴乱,令他们初到江南举步维艰。
是沈长瑾三天三夜清查知府账目,再由他带着禁军挨家踢开账上富商粮仓,总归解了燃眉之急。
危难临头,最是能看清人。谢明霁不知沈幼宜为何愿意反水帮他们,总之不会是首辅授意。
赈灾江南,抚恤百姓。如此功绩,外人看来太子殿下借此彻底在朝中站稳脚跟。但赈灾的凶险多变,百姓的无声血泪,又有几人能知?
沈长瑾的确有犯律法,但她从未贪污、鱼肉百姓。依谢明霁之见,功过相抵,可从轻发落。
“朕自然不会要她性命。”
纵是震慑陈党,也断不会拿她作例。
如此,谢明霁施礼告退。
御书房中归于宁静,元朔帝望书架上几处涉案的乡试答卷。从元和十五年至三十年,分列置于其中,有些因地方保存不当,业已泛黄。
在见她之前,他尚有一事未明。
她无依无靠,面黄肌瘦,衬得那双眼睛愈发大而可怜。
沈幼宜望战战兢兢的女孩许久,下定主意般带袁秀回京。
沈府虽小,总能养得起她。
彼时的元朔帝神色复杂,他们奉旨南下赈灾,一路奔波。除了淮阳府,淮安府、清平府灾情更甚,带上袁秀随行,实在是将她置于险地。
“孤会命人另行将她安置,不必忧心。”
她披了太子的斗篷,愣愣看他。
太子殿下没有食言。等到沈幼宜回京时,袁秀已经由东宫的管事安排,被皇庄一对夫妇收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