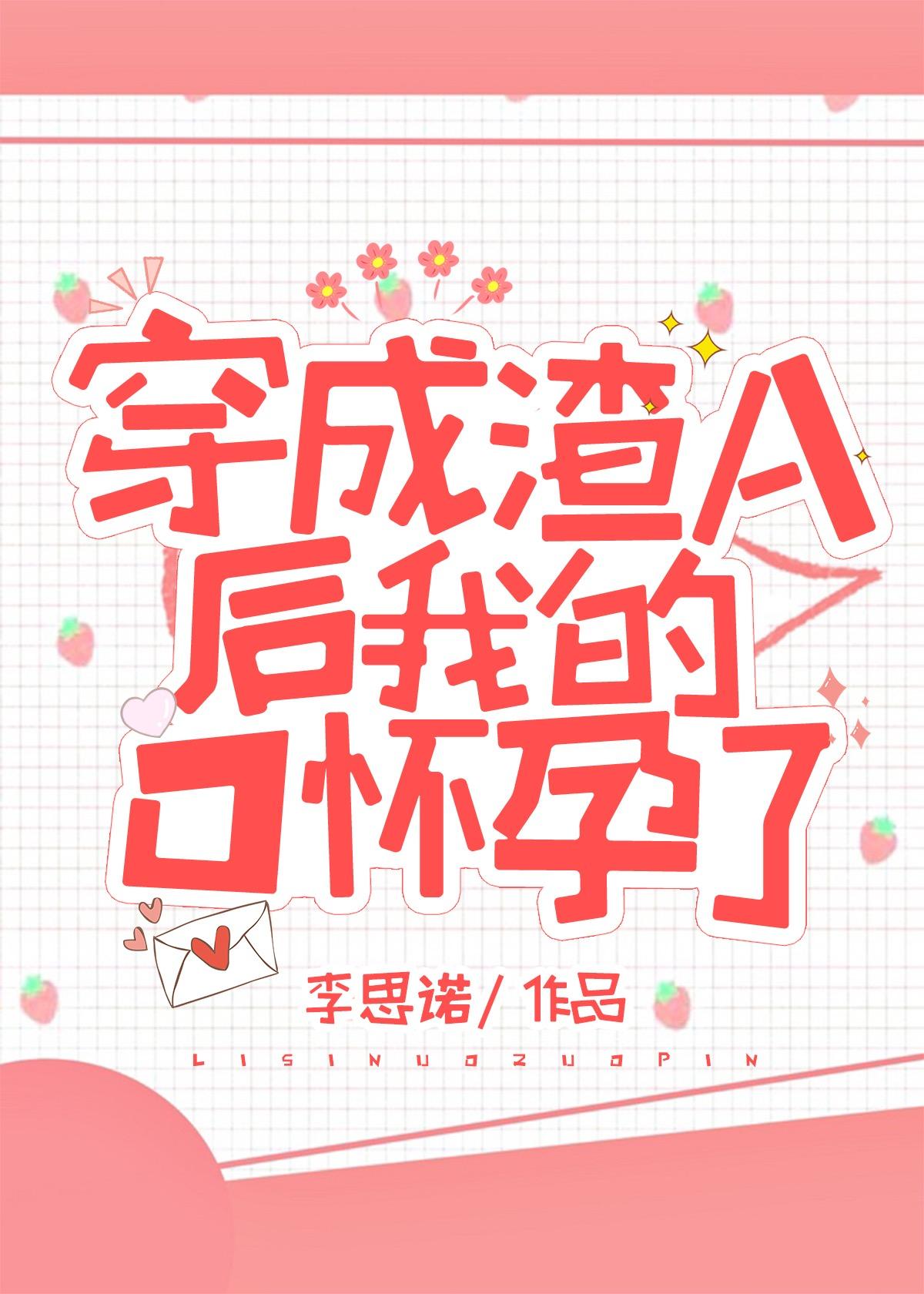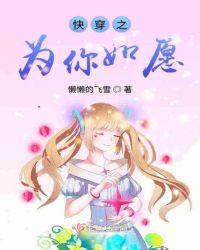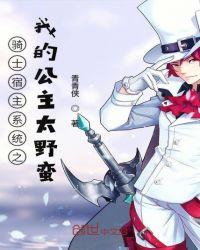69中文网>念念不忘 > 第77章 心扉(第2页)
第77章 心扉(第2页)
宋尔佳道:“对啊,我不开心了,和人打个电话说一说,虽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心情就是会好很多,所以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她觉得阮祯很好很好。
经济独立、情绪稳定、心智成熟、体贴温柔,这些特质,阮祯身上都有。
谁不喜欢这些特质呢?
但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才会被喜欢?才值得被喜欢吗?
不见得。
这不能说明对方完美无瑕,是理想型,只能说明彼此存在一定的距离感,其中一方向下兼容了另一方。
她要喜欢一个活生生的、有情绪的、有自我的人,而不是一个俯视她、包容她的人。
她要平等的对视,她要互相兼容,要彼此有来有往,势均力敌。
宋尔佳继续柔声说:“为什么总要一个人去承担呢?以后试着和我说一说好不好啊?现在说不出来也没关系,慢慢来,用时间证明,我会陪着你很久很久,反正我都等你那么多年了,不差这一时半会的。”
夜已深,卧室开着微黄的暖光灯,身边人的嗓音很温柔,温柔到阮祯忘了接下来要说的话语,只觉被温暖的灯光笼罩着,被温柔的话语抚慰着,身心皆是暖意融融。
似乎许久未体会过这种感觉,家一般的温暖。
她出生在一个山沟沟里的小县城,记忆中,回家的路总是带着泥泞。
父母很忙,在家的日子不多,她在外面要是被其他小孩欺负了,回家诉说,无人在意,慢慢的她就不说了,学会了沉默。
但不在意不代表父母不爱,她的父母,是很典型的中国式父母,他们对子女的爱是沉默的,厚重的,乃至自我牺牲式的爱。
十岁时,她和母亲吵架,中午赌气不吃饭,直接去了学校,下午第一节课下课,心里还藏着委屈和忿忿,有人把她喊了出去,走到校门口,她看见母亲有些佝偻的背影和手上拿着的一块面包,朝她笑着挥挥手。
母亲不会和她道歉,只会担心她饿着肚子,给她送来一块面包。
之后一场天灾,地面像是掀起巨浪的海水,淹没了她的父母和亲友,她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他们的尸体,对她照顾有加的师长也化成一座座坟茔,一夕之间,举目无亲。
人情冷暖,生离死别,她在少年时期早早经历。记忆无法抹去,疼痛却可被时间抚平。她和一群同她一般的孤儿在安置基地渡过了青少年期,一波又一波的社会人士到来,投向怜悯的眼神和短暂的关爱,与之同来的,还有摄影机的闪光灯。
青少年正是自尊心最强的时期,可在现实面前,尊严变得不值一提,她只是被施舍、被赠予、被关爱的对象,那些热切和关注,就像一盆浇到冰雪上的滚烫的水,浇得她浑身不自在。
于是越发沉默寡言。
学习成了最单纯的乐趣,兜兜转转,从小山沟里的县城,考上省会的大学,她需要辗转换乘许多交通工具。到了大学,这个城市有很多她没见过的东西,脸上的窘迫和拘谨,旁人一目了然。她不表达,周围的同学便对她知之甚少,只有师长看到她的籍贯时,才会露出一丝讶异和满眼的怜悯。
那些年,怜悯对她而言,变得稀松平常,却像又在告诉她,你和别人不一样。
这份不一样,在节假日到来时,尤其明显。同学回家团聚时,她无家可归,照常外出,勤工俭学;期末结束,她最后一个拖着行李箱离开,回到空荡荡的县城板房中,一个人过年。
在学校,她学了很精神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她将那些理论知识运用在自己身上,自我排解,自我消遣负面的情绪。
后来大学毕业,考上了宋葳的研究生。宋葳知晓她的身世,亦是讶异,可或许因为专业的缘故,宋葳没有表露太多的怜悯,只是给了她一份工作,让她辅导宋尔佳的功课。
从那时起,她不再是被怜悯被关切的对象,好像她也有了资格,去关心关爱别人,宋尔佳也变成了她眼里的“不一样”。
这个女孩,活泼、跳脱,洋溢着成年人没有的朝气,像一株野蛮生长的、带刺的花,有点扎手,带着少年人纯真的良善和温软的鲁莽。她在这个女孩身上倾注了很多,以至于,越过了该有的道德心理界限。
也曾试图逃离那道界限,毕业后,身背负罪感,去了另一个城市。从小到大,角色在不断转换,在另一个城市,她成了正式的医生,医生这份工作,本就是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她有了更多机会,去治愈别人。
而她已沉默了太久太久,封存了那些不好的记忆,早早学会了自我排解那些消极的情绪,不必向谁倾诉,不必依赖谁,这样很好,很独立。
唯一放不下的,只有当初那份含蓄而朦胧的悸动。
重回这个城市后,身份再次转变,不是她的辅导老师,只是一个故交,她试着放下束缚,遵从心底的感觉,和这个女孩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如今这个女孩,站在她未曾敞开的心扉外,礼貌而又温柔地敲了敲,让她邀请自己进来。
这么多年过去,她不知道,要用多久的时间,才能从沉默学会倾诉、适应倾诉、习惯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