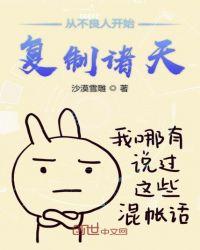69中文网>昭白雪 > 投喂(第2页)
投喂(第2页)
谢昭急急争辩:“这几天你也没好好陪过我呀!”
“……”
他自知失言,红了耳根垂下头。
李清白嗔笑:“你何时轮到和自己的儿子争宠了。”
谢昭攥紧她衣袖,低低道:“你别走。”
李清白盯着他红一阵白一阵的脸,不明白这个雷厉风行的大盐枭,为何在监狱里关了几天,就变成了这么个唯唯诺诺的小孩。
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了:“好,我好好陪陪你。”
谢昭一副讨到糖吃的表情:“嗯嗯。”
……
这一夜,谢昭睡得无比安稳。
他一向睡眠不佳,稍有棘手费神之事总会思虑颇多,以致整夜无眠。可自从与她亲近了关系,他只觉心头那口枯了多年的古井开始涌水,和她有关的点点滴滴汇成涓涓细流,一刻不停地滋养着他。
只可惜一大早许灵阶便差人来叫他,要他一同去乐韵阁听戏。昨夜她梦中呢喃的美食,他一道也不敢遗漏,命人快些做好了送去给她,好叫她心情舒畅。
许灵阶这趟来太州,除了交际便是游玩,似乎并无要事,令他好生奇怪。可这狗官向来心思深沉,无人猜得透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也只能随侍身旁,悉心观察取证。
好在元旌及时赶回,向他报告了重要消息——他重金广纳线索,问出盐船出事当晚,有人曾目击盐帮的人在河道附近出没。
帮派斗争向来是大鱼吃小鱼,这一带有实力与谢昭抗衡的唯有虎啸帮。因此,他让元旌早做准备,打算午后便扮作寻常商人,冒险登上海陵岛查探。
吩咐完细节,他便命人包下乐韵阁的场子,备好许灵阶爱吃的细点——玫瑰酥、松子糖和刚出炉的蟹黄烧卖,都用温笼煨着,再去恭请这尊大佛。
乐韵阁临水而建,是太州城里顶热闹的所在。谢昭引着许灵阶入座时,台上软糯的淮腔正唱着《珍珠塔》里的“跌雪”一折,许灵阶不多时便听得摇头晃脑,指尖在桌上轻叩着板眼,目光似在台上,又似落在别处。
谢昭不敢听戏,凝神关注着许灵阶的一举一动。果不其然,一盏茶还未饮完,许灵阶便朝他发问上了:
“阿昭,我听说,上月月末你从丰纯场支的那批盐,无缘无故不见了,有这事吗?”
“是的,大人。”
“什么人这样大胆,敢动你的生意?”
“还在调查当中,大人不用担心。”
许灵阶倏地停下了叩击。
“哦?”他眼皮微掀,从鼻腔里慢悠悠哼出一声,“那么,你这月孝敬我的银子,怕是要折损不少咯?”
谢昭额上沁出一层冷汗,将身子又躬低了几分:“必不会。小人处处倚仗大人,哪怕变卖产业,也不敢误了您的事。”
许灵阶伸手去拈碟里的玫瑰酥,却不送入口,只捏在指间细细地看,突然啪地一声将它捏碎,酥皮洒落一地。
他起身拍拍干净,踩碎满地狼藉,重新恢复笑容:“那我就放心了。”
谢昭盯着那些被他鞋底碾碎的粉末,想起了很多人。
盐运司同知赵文华,只因秉公核查盐引数目,一周内被弹劾七次,发配贵州充军,未及到达便死在了路上。
太仆寺少卿李默,只因议马政时顶撞了首辅一句,转头便被锦衣卫从直房里请走,从此下落不明。
户部右侍郎张简,只因谏言停修仙殿,便被扣上“阻挠国计”的罪名,诏狱里关了不到三日就传来死讯,据说尸体被抬出时,浑身找不到一块好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