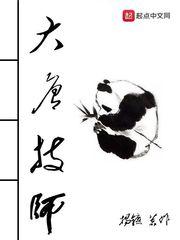69中文网>娇弱小公主竟在朝廷一手遮天 > 第八章(第2页)
第八章(第2页)
“殿下,太子殿下他只是。。。。。。”
可这话还未出口他便哽住了,只是什么?难道他就真的信了太子那番言辞?信他从此以后再不会贪墨?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见他沉默,朱予柔转身,合上双眼,决绝的声音中透着失望与无力,道:“沈川,当初的诺,是你首先背弃,城外的学子们,也是你对不起他们。自你回京后,你我已争论数次,既然立场不同,也不必争辩对错,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看着朱予柔离去的背影,沈川不由自主的向前走了两步,又很快顿住。
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她说的一切难道不是事实吗?是他选择替太子隐瞒,亦是他将罪责都推到程敏一人身上。既然如此,她选择分道扬镳,岂非是作茧自缚?
他是想辅佐太子、保佑江山,可若登上帝位的是这样一个人,他还应该继续助纣为虐吗?
就连如今她主动选择疏远,不也是他想要的吗。
所做的事情都实现了,他应该高兴才对啊。
可沈川知道,自己心中只有失落。
从督察院出来,朱予柔便一刻不停的向户部走去。
如今的她已正式成为户部主事,是该去户部转转的。
“陈伯父。”进了户部,朱予柔也不多停留,一刻不停地向户部尚书陈元升值房内走去。
这位陈尚书与李贵妃家中兄长乃是世交,自李贵妃上京后亦帮了不少忙,故而朱予柔私下一直唤他为伯父。
“老臣参见殿下。”
尽管如此,陈元升的礼数却从未短缺。
朱予柔急忙扶起他,道:“伯父快起,从今以后柔儿便是您的下属了,还望伯父多多照顾。”
“殿下,您当真要入仕吗?这入朝为官虽看着光鲜亮丽,可这其中难处亦非寻常啊。”
“伯父,柔儿决心已定,您就不必再劝了。”朱予柔温声道。
见她态度坚决,陈元升叹了口气,开口道:“也罢,其实从一开始你母亲将你教的方方面面都出类拔萃,我便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也曾劝过她,说你一个女孩子就不要掺和到这里来了,安安分分的做个小公主,将来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说到这,陈元升又摇了摇头,继续道:“可惜她不听啊。”
朱予柔笑道:“是,母亲将我引到这条路上,便是想让我有多几种选择,将来不必只能做一名任人摆布的花瓶。”
“也好,其实前些日子在殿上,你挺身而出为那些学子证明时,我就知道你母亲做的是对的。”
提到此事,朱予柔心绪纷乱,半晌才道:“伯父,我知道朝廷每年真正收到的税,往往不足百姓所交的半数,那另外一半全被官员中饱私囊。此次科举案更是能反映出我朝贪墨之风盛行。”
“这几年江南地区大规模蝗灾,武昌、河南多地又有水灾,再加上边境战乱不断,实在是令户部无能为力。予淮曾多次给我来信,说边地苦寒,发给将士们的棉衣却薄的厉害。可若不是送到地方的银子短缺,这大江上的堤坝又怎会修了再修,边军又怎会因着军粮短缺而被迫退兵?”
“虽说近年灾害频发,可对比开朝初依然下降不少,伯父,这究竟是为何?”她一口气说了许多,将心中所想尽数宣之于口。
听她所言,陈元升亦有些茫然,道:“虽说朝廷税收降得厉害,可降得最多的还是盐税,不知为何,竟还不及开朝半数,臣也曾上书陛下,下令去查,可这地方每次不过说是私盐泛滥,他们管不了,最终也没能查出什么。”
“且这盐政复杂,多少官员掺和其中,就说占比盐税一半的扬州盐政,官商勾结极其严重,藏着半个朝廷的官员纠缠,陛下不想动摇朝政,便只能看着他这么腐坏下去,别无他法。”
虽然早就知道朝廷腐败,但今日算切实了解了其中关键,朱予柔心中仍掀起不小的波澜。
她暗自琢磨片刻,问道:“那依伯父所说,只要能处理好扬州的盐税,便可解决不少麻烦?”
闻听此言,陈元升心中一惊,猜到朱予柔的意图,说道:“殿下,您虽贵为公主,有陛下护着,他们等闲不敢对您下手,可您要真触动他们的利益,谁知那些人会做些什么,万不可行险啊。”
朱予柔嘴角苦涩,知道自己真查了扬州,必定凶险异常,陈元升是为她考虑。
然而……若连她也不敢查,这天下也无人能查了,难不成她就这么放任不管了吗。
她勉强牵扯出一丝笑意,对陈元升道:“多谢伯父提醒,柔儿记住了。”
知道她仍有查贪之意,陈元升对她道:“殿下,其实这京城之中的贪官便不少,若殿下能让他们伏法,也算是济世安民的功德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