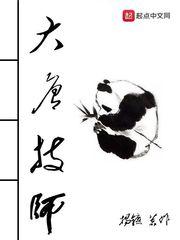69中文网>春锁凤台 > 真相(第2页)
真相(第2页)
柏姜有些遗憾,但还是听她的办了,升她为执金吾(执金吾的长官),如今宋阿濡倒了,柏姜这个手里握着唯一皇帝血脉的年轻太后终于在众人眼中举足轻重起来,都知道陈午是她干姐姐一样的人,现下出入宫禁都得巴结着,方便的很。
“宋阿濡呢?找得如何?”柏姜又问。
陈午摇摇头:“没有踪迹。”
柏姜呷一口茶,半响道:“悄悄的,让廷尉寺的人把嘴闭紧了,让宋保去审刘全安。”
“娘娘你这是要……”
“不抓到宋阿濡我始终心里难安,何况刘全安一向嫉恨宋保,难保他不会情急之下吐出什么有用的来。让宋保去审,或许只有太监才对付得了太监。”
陈午将茶一饮而尽,作势要告退,柏姜纠结再三,最终一把抓住她手腕,陈午回头:
“嗯?娘娘还有什么事?”
柏姜眉头微蹙:“你刚刚说,宋阿濡很爱惜宋保?”
陈午点头:“是,脏活儿都是刘全安在干。我在执金吾,大多在城墙根儿底下,娘娘你在宫中,自然比我见得更多。”
确实如此,柏姜握着陈午的手渐渐加重:“再派一个人,去盯着宋保,一旦他有什么偏袒那老阉官的言行,即刻杖杀,对外就说自裁于狱中。”
这下换陈午皱起眉:“阿姜,他应当不会……”
柏姜拍拍陈午的手背:“以防万一。”
刘全安刚受了鞭刑晕了过去,忽地周身一凉,继而全身的伤痕都火辣辣地灼痛起来,他神志不清地咒骂着:“柏姜——狗娘养的,不过是一个南朝俘虏、一个下贱婢子!竟也敢、竟也敢……”
他不期然看见一双熟悉的锦鞋,于是停了口中对柏姜的污言秽语,愣愣地抬起头来——竟然是宋保。
宋保在狱中没怎么受罪,刚换了一身新衣,如同替他干爹来狱里视察一般,金尊玉贵地站在他面前。
刘全安激动起来:“你……你为何没有受刑?!你难道背叛了干爹,转投在那小太后的门下?”
宋保一甩大袖,背手走上前,正对上刘全安怨毒的眼神:“何来背叛,我本就是太后娘娘的人。”
“当年我家破人亡,是太后娘娘心慈,命陈大人救了我,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刑房里传来刘全安声嘶力竭的辱骂,不知宋保用了什么刑,刘全安口中言语渐渐不成词句,被撕心裂肺的嚎叫所取代。
外间里,女使受不了了似的捂起耳朵,一旁刑官陪着笑:“这宋保看起来还算老实。”
女使冷淡地“嗯”一声:“劳烦大人带我出去,好向太后娘娘复命。”
“好好好,请。”
这两日柏姜蓦地忙起来,不是忙宋阿濡的事,毕竟朝堂上一堆官员正如同饿虎扑食般竞相检举、痛打这曾经的权宦,狠狠地抒发了压在心头多年的恶气。
他们在朝堂上出力,他们夫人也不闲着,皇帝多病,不大管政事,命妇女眷们便想方设法地往柏姜这边使力,往日门口罗雀的长乐宫忽而门庭若市,柏姜迎来送往倦的很,又不能推脱,心里十分的郁闷。
这日好不容易应酬完了人,柏姜躲去林苑里赏雪,再有来拜见的一律不见,如此挨到晚间,柏姜舒坦了,叫阿充找人递消息给阿午,留她在宫里吃晚饭。
没想到陈午今日也得了宋保的消息要进宫。
夕阳西下,暮云四合,被落日映得金黄的宫道上拖着长长两道人影,一男一女,竟是陈午和李璋。
柏姜惊讶地与阿充对视,继而叹道:“往前也就是咱们不得势,如今日子好些了,便有那男人苍蝇似的来扑你姐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