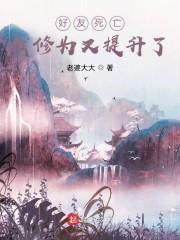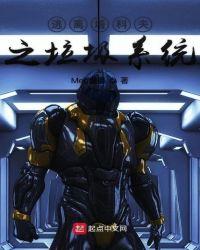69中文网>[水浒]我靠写野史诏安梁山 > 我水月娘子(第3页)
我水月娘子(第3页)
说书先生点头如啄米:“应当,应当。”
“第二,我不喜别人改动我的文章,你要按原稿来讲,把主角换成女将军穆桂英。”
“可您那原稿写得有些忒大胆,穆氏……穆桂英身为女子,生擒夫婿,活捉阿翁……这……”
“有什么不妥吗?”
明镜一抬眼,那说书先生立刻道:“妥当妥当,我保证按话本来讲,但如果听家不满……”
“第三个要求就是,请先生说完书后提一句,故事是我所作,听众若有异议,也不会算到你的头上。”
“如此甚好,敢问娘子尊讳?”
要起个什么笔名呢?
明镜脑子里瞬间滚过一堆类似于“我爱写文”“给我吃饭”“自割腿肉”之类的名字,又默默否决。
要不然化用前辈的名字,叫个什么“清风镇笑笑生”?好像也不太庄重。
总不能直接叫本名吧?
明镜皱眉苦思,突然余光瞥到墙上挂画,画中一妙龄女子坐于破席,揽镜自照,窗外铁青青一钩弯月,屋下稀落落几瓶败花。
明镜煌煌,照尽千娇百媚堆;水月溶溶,浮沉万点琉璃碎。故事说到最后,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她心中忽地动了动。
“你就说是,水月娘子所作吧。”
说书先生刚应下,前面观众却早等不及,连声催促起来,老头连忙拿了扇子起身上台,开始翻动三寸不烂之舌重讲话本,留下明镜两人等着小童取钱过来。
没多会儿,小童吃力地搬出一个小筐:“喏,一足贯的铜钱,剩下的我再去取。”
明镜眼前发黑,暗道不妙。
自从穿到这个朝代,吃穿用度花的都是知画怀里那袋子金银。
因而她对钱没什么概念,开价时考虑到说书人可能没法拿出银两,就想着要些铜钱方便花,压根没想到两贯钱有这么沉。
知画发愁道:“娘子,这可怎么拿?”
两贯钱好比两个七斤重的大圆西瓜,坠得人胳膊发疼,如果直接端出去,说不定还没走到半路上就被抢了。
她叹口气,绝望道:“有等价的银两吗?”
小童眼珠一转:“只有几块小银,合一两有余。”
徽宗时期金银价值都在上涨,铜钱反而贬值,两贯钱换一两银子,也不算亏。
“好,那就拿银子吧。”
终于历经坎坷赚到第一桶金,明镜步履轻快地走出瓦子,却见前方街面上不少人围成个大圈,似是在看什么热闹。
知画好奇地垫脚张望,忽然道:“欸?那黑汉子不是刚和您一同饮酒的官人吗?”
明镜猛地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