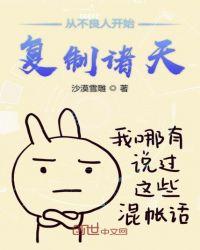69中文网>纨绔死后第五年 > 第十章(第3页)
第十章(第3页)
他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偷偷潜入了简家祠堂,偷渡了好几块肉饼糕点给他,又拿了护膝来,让他歇歇脚。他想不明白,简知许那么乖了,还会因为因为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情被罚,阿爹怕是做梦都想要简知许这样聪明伶俐的孩子吧。
起初简知许死活不肯,但毕竟是孩子,也有跪累的时候,耐不住江扶舟在旁边叽里咕噜鼓动半天,勉为其难地吃了半块糕点,便俯身再跪,十足诚心敬意。
看得自小就不服管教的江扶舟是瞠目结舌,于是扑通一下也跪在了蒲团上,磕了个头,“简家老祖宗,你快睁眼看看吧,简知许因为一个错字就被罚过祠堂,简直天理难容。”
这一套操作让简知许傻眼了,听到江扶舟的话又觉得好笑,但很快想到这是在祖宗祠堂,马上又收敛了,咳嗽了一声,“我阿爹当年写错了一个字被打了十大板,躺了十天半个月没下床,我才只是跪祠堂,已经是我爹宽容了。”
江扶舟挠了挠头,“你们家好严,那我这种老写错字不是得打上五百板才够。”
一句话成功把简知许逗笑了,“你又不考状元,担心这个干什么,勤加练习,定能有所进益,若你愿意,我可以教你。”
听到写字读书就头疼发晕的江扶舟立刻拨浪鼓似的摇起了自己的头,但他很快产生了疑惑,“状元很简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可以考到呢?”他凑近了些,“我听说一次科考全国就一个状元呢。”
简知许有些腼腆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家中的族老伯叔都说我有状元之才。”
江扶舟佩服地拍了拍简知许的肩膀,然后装模作样地给他作揖行礼,“简状元,以后要多多关照我才是。”
简知许被他这一套将江湖习气的动作弄到手脚无措,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突然被江扶舟又塞了一块糕点在嘴里,“一天两个馒头怎么够,先填饱肚子吧,状元!”
多年后简知许真的一甲及第,不过他考上的是榜眼,那年的状元是他俩的好友宁遥清。这一件事让简家的族老乡亲叹惋了许久。
如今大家都近而立之年,简知许已经是国子监司业,清正端直,素有雅名,而徐方谨还在给简知许当学生,真是因缘际会,不可名状。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简知许手上拿着最后一张课业,忽而出声。
徐方谨低头恭谦,“学生犯了错,不该参与到私下群斗之中。”
“你并无过错,我罚你可有异议?”
“无论如何学生就是牵连到其中来,大人公正严明,学生不敢有半点怨言。”
一番对话听得简知许心头莫名的火气燃了起来,他这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期待什么,藏于袖内的拳头紧紧握住。
“四年前你经林渠大人举荐得以入府学,可我听闻你之前不曾有志于科举。”
同样的问题徐方谨把他对沈修竹的话又委婉地说了一遍给简知许听,可他怎么感觉简知许越来越生气了。
“学生可有说错?请大人指正。”
简知许语气生硬地回他,“没有。”
接着又问,“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徐方谨这下给简知许搞不会了,交浅言深,他们不才初次见面吗?怎么还评价上他了?他现在是个学生,能当着面说老师什么?还指望他跟从前一样勾肩搭背,说话不分轻重吗?
他立刻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学生实在不敢妄议尊师。”
简知许被他这幅卑躬屈膝,惺惺作态的样子气到心头发闷发痛,眼底里的郁气又重了几分,“三日之后就去刑部历事,出去吧。”
徐方谨恭敬告退,然后蹑手蹑脚地出去,还好心地给简知许带上了门,心里却不自觉犯嘀咕,简知许怎么这样,脾气越来越差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国子监里纨绔子弟不少,整日惹是生非,再好的脾气也会被消磨,如此便又原谅了简知许。
却没看到简知许看到他动作时的沉默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