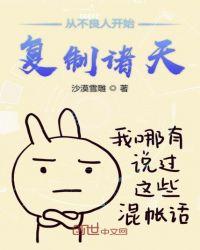69中文网>天幕:玩县令模拟器被围观了 > 失魂落魄小药丸(第1页)
失魂落魄小药丸(第1页)
夜幕低垂,县衙旁唯一一间酒肆灯火通明,喧嚣的人声驱散了寂静的街巷。
如李景安所料,王有财和张贵的“压惊宴”如期开场。
可出乎意料的是,李景安非但没推脱,反倒欣然赴约。
甫一落座,他便含笑拍了拍张贵的臂膀,声音低沉恳切。
“王县丞,张书吏,昨日仓促了些。云朔水深路险,景安新来乍到,日后衙中事务,还需王兄、张书吏及诸位前辈多多指点提携。”
“这些年县衙井井有条,全赖诸位操持,此功此劳,景安铭记于心。”
“今日前来,一为昨日惊扰赔个不是;二来,也是想与诸位亲近。日后同衙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分忧,景安年轻,少不得要仰仗各位帮扶,凡事还望不吝赐教。”
他一边说着,一边目光状似不经意地扫过满座宾客。
烛光摇曳,一张张或精干、或油滑的面孔在光影中晃动。
李景安心底冷笑,白日里沉甸甸列在【列陈】上名字,此刻正如此鲜活地坐在眼前,推杯换盏。
面上虽仍是春风和煦,心头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一个两个三个的都来了。
很好,不用他费心了,谁也逃不掉。
张贵瞧着态度如此“诚恳”的李景安,心下不禁纳罕。
这人莫非属两面蛇的么?
怎地昨日在白日堂上还一副铁骨铮铮、六亲不认的清官模样,一夜之间就换了个面目?
言语间流露的亲热谄媚劲儿,竟比他经手过的历任县尊都要熨帖?
虽说满腹狐疑,但到底官大一级压死人,张贵断不敢落了知县的风头,赶紧堆起满面笑容,举杯高声道:“大人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折煞下官了!”
“云朔小县能得大人垂顾,实乃百姓之福!昨日小事,大人何须介怀?我等本分当差,替大人分忧解难罢了。”
“日后县衙上下,唯大人马首是瞻!衙中琐事,自有我等效力,只求大人信重!来,大伙儿敬李大人!”
话里话外,都透着日后共同“发财”的暗示。
李景安笑呵呵地应了这通马屁,顺手端起面前的酒杯,指尖在光滑的瓷沿上轻轻一叩,发出微不可闻的脆响。
身后如木桩子般站着的木白,瞬间会意。
他悄无声息地上前半步,稳稳接过了小二手中的酒壶。
就在身体微微遮挡的刹那,他指尖微不可查地一抖,几滴清冽如水、无色无味的液体精准地融入刚为李景安斟满的酒中。
木白随即作势要转向张贵斟酒。
张贵受宠若惊,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要去拦:“哎唷!大人!这怎么使得!不敢劳烦……”
“张书吏。”李景安虚拦,笑意带着“歉意”,“让他斟酒赔罪,也是该的。”
他说罢,举起那杯“酒”,声音十二分“诚恳”:“昨日行事,是景安年轻急切了些。”
“初来乍到,总要做个样子给百姓看,权当立个名声,无奈扰了诸位雅兴,还望海涵。”
“我自罚三杯,权当赔罪!”
话音未落,李景安已干脆利落地仰头,将那杯“加料”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从木白手中接过两杯,毫不犹豫地灌下喉咙。
三杯“诚意”下肚,清隽面庞迅速漫开大片绯红,如同擦了京城里最上等的胭脂。
他微晃了下,眼神迷离地转向王有财和张贵,脸上酡红更深,带着醉后的“推心置腹”。
“王县丞……张书吏……”他嗓音微哑,身子还向前倾了倾,“白日里……是下官……太过急切了!终究是初来乍到啊!”
“这云朔的天高地厚……规矩路数……人情世故……小弟我……还需历练!往后……衙门里外……大事小事……都……都赖诸位前辈了!”
说完,他垂下眼,几乎是带着一丝“羞愧”,将杯底那最后一点残酒狠狠灌入喉咙。
张贵摸着溜圆的肚子,小眼睛眯成一条缝,与旁边的张贵飞快地碰了个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