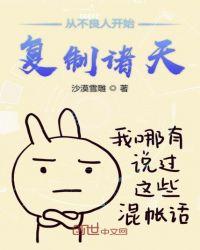69中文网>天幕:玩县令模拟器被围观了 > 失魂落魄小药丸(第3页)
失魂落魄小药丸(第3页)
“我……我加征‘修桥税’,钱都进了我的腰包,桥影子都没见着!”
“我……我收了钱,把告状的陈铁匠儿子硬生生打成残废!”
“我,我还占了那老穷民陈长顺的女儿!得手了,还不知珍惜,如今就关在那地窖里,不知道死活了。”
“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该下油锅啊——!”
一扇扇黑漆漆的窗户后面,瞬间亮起了豆大的油灯光。
窗户纸被手指头悄悄捅破,无数双眼睛惊疑又愤恨地盯着街上那个癫狂的身影。
“呸!天杀的!”
巷尾传来压抑的啐声,是卖茶水的刘老汉,他的小茶摊就是被张贵的小舅子硬生生占去的。
“真知道罪过,去衙门投案啊!在这嚎丧顶个屁用!”
斜对门开杂货铺的李二胆子大些,隔着窗户吼了一嗓子,声音带着压抑多年的恨。
“衙门?”
立刻有人接腔,是住在城隍庙边的孤老张头,声音嘶哑。
“那衙门儿跟他穿一条裤子!早沆瀣一气,烂到根儿了!去了也是羊入虎口!”
张贵听见议论,猛地抬头,脸上血泪模糊,眼神却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透着股诡异的狂热:“不……不一样!新来的……李县令……他……他厉害!他不收钱!我看不透他……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这话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所有偷听的人心头一颤。
刘老实家中的事情没防着人,县太爷助他的事情传的到处都是。
难不成真来了个好官?
“那你倒是去啊!”一个年轻的声音喊道,是常在码头扛活的孙大壮,“去县衙自首!让大伙儿都瞧瞧,那新县令到底是青天还是王八蛋!是真不是一窝,还是搁这儿演戏呢?”
“对!去!我们跟你去!给你‘作证’!”
几个平日里被盘剥得最狠的汉子按捺不住,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站到了昏暗的街上,手里还拎着扁担、柴刀,眼神像刀子。
“好……好!我去!我去自首!”
张贵挣扎着爬起来,像条被抽了筋的癞皮狗,踉踉跄跄往县衙方向跑去。
“我罪孽深重……需要人证!谁来……谁来作证?!”
孙大壮啐了一口,招呼着几个相熟的汉子,不远不近地跟了上去。
更多的门悄悄打开,无声的人流汇入夜色,沉默地涌向县衙,像一股压抑已久的暗潮。
“咚——!咚——!咚——!”
深夜的县衙,沉寂被急促如暴雨的鼓声撕裂。
那鼓槌仿佛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公堂之上,灯火通明。
李景安一身青色官袍端坐明镜高悬匾额之下,脸色在烛光映照下愈发显得苍白,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像寒夜里的星子。
他尚未开口问话,堂下跪着的张贵便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头磕得砰砰响,涕泪血糊了满脸,将方才在街上的忏悔,加上更多更隐秘、更令人发指的罪行,如竹筒倒豆子般,一字不漏地倒了出来。
如何强占孤女为妾逼死其父,如何克扣河工口粮导致溃堤淹了半个村子,如何与山匪勾结坐地分赃……
桩桩件件,血淋淋,臭烘烘。
李景安静静听着,搁在案上的手,指节早已捏得发白,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一股压抑不住的闷意堵在胸口,让他呼吸都变得艰难而短促。
他下意识地抬手,冰凉纤薄的指尖按在微微起伏的心口处,似乎想平复那无名的窒涩。
唇色愈发显得浅淡,甚至有些泛青。
公堂上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层水雾,他努力集中精神,但眼前却时有微小的黑点掠过,带来阵阵眩晕。
每一次沉重的认罪声,都像压在他紧绷的神经上,身体不自觉地微微晃动,宛如风中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