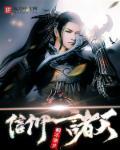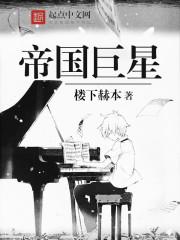69中文网>归义非唐 > 第543章 革故鼎新(第5页)
第543章 革故鼎新(第5页)
“此外京畿道判决既然已经下来,那便先开始造势,让各地报社将此次殿下所查案例、判决,择其典型,刊印成册,发于报纸之上,以示朝廷绝非滥施刑罚,而是有法可依,有罪必惩。”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一条清晰而冷酷的战略逐渐成型。
以放宽标准扩大打击面,以新生与沉沦之吏为爪牙,以明发律令为旗帜,最终达成皇帝所需的“人口”与“田地”两大目标。
刘烈听着三位属官将一项项细则完善,原本凝重的脸色也渐渐舒展,最后笑着点头道:“如此便依诸位先生之策,只是还需要劳烦诸位先生奔波。”
“郭先生,劳你即刻草拟征调学子与临州旧吏的章程。”
“严先生,由汝主持官吏从《大汉律》中挑选条例,拟定《京察天下诸道量刑则例》,将标准明晰。”
“赵先生,以报社报纸引导舆情,行刊发之事,便交由汝统筹,此外再请卢先生将京畿之事妥善解决后,立即带领京畿道诸多京察队伍听令,等待入剑南道京察。”
对于刘烈的安排,三人齐齐躬身:“臣等领命!”
刘烈看着他们,郑重拱手:“孤之前程,大汉之社稷,尽托付于三位先生了。”
郭崇韬、严可求、赵光逢三人连忙作揖回礼,接着便在刘烈注视下离开了东宫。
“噼里啪啦……”
腊月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新年的喜庆气氛却被另一种更加炽烈的情绪所取代。
洪武十二年的开端,神都洛阳的街巷里弥漫着的,不再是年节的欢腾,而是一种压抑的嗡嗡低语。
自洪武三年刘继隆力排众议,在天下各州县广设官学以来,如今已是第九个寒暑。
寻常百姓家的孩子,纵使无法如富家子弟般十年寒窗求取功名,但也能送进去读上两三年书,识得几百常用字,会写自己姓名,看懂官府告示。
这点滴的教化,于国而言是开启了民智,于民而言则是多了一扇窥见世道的窗。
正是因为天下官学推广,因此朝廷开办的报纸才能被平民所读懂,为平民添了处看不到的风景。
这报纸在此前并未展露什么威力,可随着洪武十二年到来,正月新年这期报纸却登载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内容。
《国报》与《京报》的头版,赫然便是《京畿道京察结果昭示天下》,其下罗列着密密麻麻的案例,判决……
这在报纸上,所有官吏贪腐和勋臣害命的案件时间、地点、人物、赃款数目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除此之外,此事末尾还有个的惊人数字,那就是此次京察共抄得钱粮五百余万贯,粮秣七十余万石,田产一百七十余万亩,其余古玩珍宝逾千箱……
识字的人在拿到报纸后,立马便说给四周不识字的人听。
他们每读出一条,四周人群中便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和咒骂。
议论声、咒骂声、诉苦声,在洛阳城的每一个茶肆、酒馆、街头巷尾中汇聚、发酵。
平日里逆来顺受的沉默,在这一刻被报纸上的白纸黑字点燃了。
他们骂那些蛀虫般的贪官,恨那些趴在他们身上吸血的勋贵,更抱怨着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公。
宰相崔恕的马车,就在这片压抑的鼎沸人声中,缓缓行驶在回府的路上。
尽管车窗紧闭,但车窗却隔不断窗外那一声声清晰的、咬牙切齿的议论。
崔恕靠在棉花粗布制成的软垫上,尽管闭着眼,可外面的声音毫无阻碍地钻进他的耳朵。
“直娘贼,某便是卖一辈子茶都卖不出这贪官污吏的碎末。”
“还是太子殿下厉害!查得好!就该把这些祸害全抓起来!”
“不知道啥时候能查到洛阳来……”
窗外的声音不断传来,使得崔恕指尖微微颤抖。
东宫那边的事情,他也曾听说过,近来许多临州毕业的学子都被召到了洛阳,并授予了都察院、六科、大理寺和刑部等处的官职。
这些种种行为似乎都在告诉崔恕,所谓京察并未结束,自家陛下的野心也并没有那么小。
到了今日,听着窗外的那些声音,崔恕总算是明白了。
陛下确实不准备就这样停下京察,而太子也即将把京畿道的这把火扩散到其他地方。
想到这里,崔恕渐渐有些不安,所以在回到府邸后,他第一时间便召来了家丞,对他吩咐起来:
“告诉族中的那些子弟,多看看报纸,近来小心行事。”
“若是出了事情,便是老夫也护不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