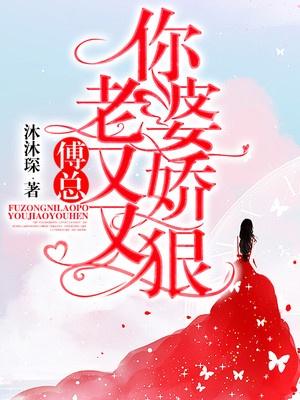69中文网>永乐帝后 > 晋王大婚和孙贵妃的一生(第1页)
晋王大婚和孙贵妃的一生(第1页)
转眼间,就到了朱棡与谢颖文的大婚之日。
这一天,整个应天府都沉浸在一片喧腾的喜庆之中。
自皇城至晋王府邸,十里长街被净水泼洗得纤尘不染,黄土铺就的坦途之上,满街满巷都挂上了红绸与宫灯。
徐仪随母亲谢佩英肃立在外命妇的行列之中,耳畔间礼乐悠扬,赞官的高唱声遥遥传来。徐仪抬头瞭望,却也只能望见皇城那高高的殿檐和招展的龙凤旗帜。
册立亲王妃的仪式,自有一套繁复的规矩,亲王妃要依次拜过帝后,宫妃,太子。这期间,公主和外命妇都只能在殿外等待。
在等待的时间里,徐仪不禁想象,谢颖文会如何在女官的搀扶下,一步步走上丹陛,接受王妃册宝。
从此以后,她的荣辱,都将与皇室,与晋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直到午时过后,宫中传来消息,晋王妃谢恩礼毕,升了王妃宝座,一应公主、郡主、外命妇等,方入殿拜贺。
此后人群向宫外散去,各自登上早已备好的车马,往晋王府赴宴。
晋王府内,早已是一番热闹光景。
管事、仆妇、小厮们穿梭如织,脸上无不挂着喜气洋洋的笑容。庭院中,席面罗列,珍馐玉液让人眼花缭乱。
徐仪随母亲步入内堂,终于见到了今日的主角。
谢颖文身穿大红翟衣,以金线绣满祥云与凤凰,头戴九翟四凤冠,脸上的珍珠流苏随着她细微的动作轻轻摇曳,映得那张略施粉黛的芙蓉面,愈发娇艳欲滴,通身的雍容与华贵,这样的谢颖文她还是头一次见。
就连眉宇间的病弱之气,仿佛也被满溢的喜悦冲刷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双顾盼神飞的明眸,亮得好似含着一汪春水。
“颖文姐姐。”徐仪上前,规规矩矩地福身行礼。
谢颖文见了她,眼中的笑意更浓了。
她连忙虚扶一把,嗔道:“何须如此多礼。”
徐仪依礼说了些吉祥话,看着谢颖文脸上那发自内心的、毫无阴霾的笑容,想来宫廷里的那一场无妄之灾,对她来说都已成了过眼云烟。
自喧闹的内堂中告退出来,母亲正与几位相熟的国公夫人们叙话,朱祥荣提前回宫,徐仪于是独自一人,沿着抄手游廊缓缓而行。
廊外,是修剪得宜的花木,几株性急的秋菊,已经绽开了金色的花瓣。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与菜肴的香气,混杂着宾客们的欢声笑语,杯盏的碰撞声、丝竹的悠扬,织成一张热闹非凡的画卷。
徐仪远远就看到一道单薄高挑的身影站在远处,她心下了然此人怕是刻意等她,避无可避,于是抬步向前走去。
—————————
入秋后的第一个坏消息传来,北平真定等地发生旱灾,陛下下旨运苏州米粮近四十万石到灾区赈灾。皇后听闻消息后,茹素两月,将珍馐省下赈济饥民。
坤宁宫内,午后的阳光透过格扇窗,斜斜地照在紫檀木的雕花长案上。
马皇后正埋首于一堆宫务文书之中,眉头微蹙,显然后宫账务繁杂。徐仪侍立一旁,替皇后研墨,身边的女官黄香莲间或递上一两份整理好的卷宗。
突然,殿外传来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
一名内侍躬身入内:“启禀娘娘,太医院张院判在外求见,说是有要事禀报。”
马皇后搁下手中的朱笔,抬起略带倦容的脸:“宣。”
张院判很快便被引了进来,他面色凝重,一揖到底:“微臣参见皇后娘娘。”
“不必多礼。”马皇后的声音温和却带着威仪,“有何急事?”
张院判直起身,脸上露出一丝为难:“回娘娘,是关于孙贵妃娘娘的病情。”他略一停顿,“微臣与院中几位同僚几番会诊,已用尽了法子,但贵妃娘娘脉象虚浮,药石罔效,已是油尽灯枯之兆,只怕时日无多了。”
此言一出,殿内空气霎时一凝。徐仪心中一沉,那位性子孤傲的贵妃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马皇后握着朱笔的手微微一紧,沉默了片刻,才轻轻叹了口气:“知道了,你下去吧,依旧好生照料着就是。”
“微臣遵旨。”张院判躬身告退,脚步沉重。
徐仪垂眸,未几,又有孙贵妃的宫人前来通传,贵妃想求见皇后一面。
马皇后正处理着几件宫中紧急的度支,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她还是点了点头:“备驾吧。”又转向徐仪,目光柔和:“仪儿,你随本宫一同去看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