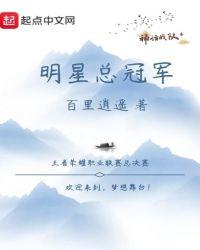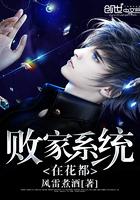69中文网>穿成带娃和离妇,盖房囤粮当首富 > 第二百一十六章 冬日(第1页)
第二百一十六章 冬日(第1页)
沈观定了定神,继续说道:“那时节,朝中后宫不宁,皇后体弱多病,膝下无子,而贵妃仗着圣宠,与其父兄在朝中培植了不少党羽,权势熏天,内外勾结,野心勃勃,一心想扶持自己所出的皇子上位,为此不惜排除异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霁侍郎为人耿直,素来看不惯此等以权谋私、祸乱朝纲之举,又因其在清流士子中影响力巨大,不愿依附贵妃一党,便成了贵妃及其父兄的眼中钉、肉中刺。”
“终于,贵妃与其父兄罗织罪名,以通敌叛国、意图谋逆的弥天大罪,设计构陷,将霁家满门一百三十余口……一夜之间,尽数抄斩!明远兄……仲晴弟……还有那些无辜的妇孺老弱……无一幸免……”
他的声音沙哑,双拳紧握,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只有……只有兄当时年仅周岁、尚在襁褓之中、刚刚会走路的幼女槐蓁,”
他低下头,轻轻抚摸着依偎在他身边、正好奇地摆弄着他衣角的沈淮的小脑袋,“因我事先察觉到一丝风声不对,又恰逢她感染风寒,我便借口将其接入我府中照料,并暗中联络了一位早已退隐田园的远亲,连夜将还在发着低烧的阿淮送出京城……这才侥幸让她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
“我沈家因与霁家世代交好,又因我暗中相助之事走漏了些许风声,也受到了牵连。我祖父被贵妃一党寻了个‘用药不当、延误病情’的由头罢了官。不久便含恨而终。”
“为了保护她,我对外只称她是……是我在外游历时所生的私生女,取名沈淮,一路辗转,最终来到了的垚县。”
“这些年来,我从未放弃过暗中查访。“
”我得知,当年霁家似乎与一批秘密炼制的兵器有关,而那批兵器的源头,隐隐指向了某个极其隐蔽的山中窝点……只是线索到此便断了。那后山的秘密,我其实也曾隐约察觉到一丝异常,只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更不敢贸然行动,生怕打草惊蛇,”
“直到……直到乡君你,将那枚刻着‘霁’字的玉佩,交到了林大人手中。”
沈观深深地看着苏玉娘,“乡君!那一刻,我就知道,或许……或许是苍天有眼!是明远兄和仲晴弟他们在天有灵!指引着你找到了这沉冤昭雪的关键!”
“正是凭借这枚玉佩,这个无可辩驳的信物,以及乡君你冒死呈报的关于后山私炼的线索,林大人和周大人才能顺藤摸瓜,将后山逆贼与当年霁家惨案联系起来,最终查清了贵妃一党狼子野心、图谋造反的真相!也才得以还了霁家一个清白!”
他说完,再次起身,就要对着苏玉娘郑重行礼。
苏玉娘连忙起身扶住他:“沈大夫,万万不可如此!我当初所为,也是机缘巧合,更是为了地方安宁,不敢居功。能为霁家和沈家洗刷冤屈,沉冤昭雪,也是上天有眼,还了世间一个公道。”
沈观却坚持行了一半的礼,眼眶湿润:“乡君,这份恩情,沈观……永世不忘!若非是你,我等冤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昭雪!槐蓁这孩子,也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以霁家后人的身份活在世上!”
他轻轻将身边的沈淮拉到身前,柔声道:“阿淮,快,谢谢苏姨。”
沈淮仰着小脸,看着苏玉娘,伸出小手,学着父亲的样子,有些笨拙地作了个揖,奶声奶气地说了两个字:“谢谢……姨姨……”
苏玉娘看着这粉雕玉琢的小人儿,心中也是百感交集,连忙将她轻轻抱进怀里,柔声道:“好孩子,不谢不谢。以后,就跟爹爹一起,好好过日子。”
一场压抑多年的冤屈往事,终于在今日得以倾诉和释然。
花厅内的气氛,也由最初的沉重,渐渐变得轻松起来。
苏玉娘让丫鬟重新换了热茶和点心上来,与沈观闲聊起来。
“那……沈大夫,”苏玉娘看着他如今清朗了不少的面容,轻声问道,“如今大仇得报,冤屈昭雪,霁家也恢复了名誉,您日后……有何打算?可会……返回京城,重振沈家医名,或是……另有高就?”毕竟以他的才学和家世渊源,若想在京城谋个好前程,并非难事。
沈观闻言,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脸上露出一丝经历了风雨后的淡然笑容:“京城虽好,却也……太过繁华喧嚣,人心也过于复杂。这些年,反倒是在垚县那清静之地,每日里行医救人,与乡邻们往来,才觉得活得像个真正的自己,心里踏实。”
他顿了顿,目光望向窗外,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又像是对未来做出了抉择:“如今,我心中最大的牵挂已了,只剩下槐蓁这孩子尚且年幼,需要我好生抚养长大。至于功名利禄,早已看淡了。”
“说实话,”他转回头,看着苏玉娘,眼中带着几分真诚的笑意,“我倒是觉得,垚县……挺好的。山清水秀,民风也算淳朴。若乡君不嫌弃,沈某或许……还想在此地多盘桓些时日,继续做个乡野郎中,守着我的医馆,守着阿淮,也……守着像乡君这样的朋友。”
苏玉娘听他这么说,心下一跳:“沈大夫能有此想法,玉娘自然是欢迎至极!往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咱们……也算是共患难过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