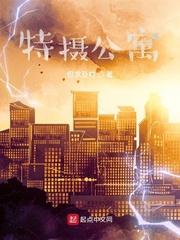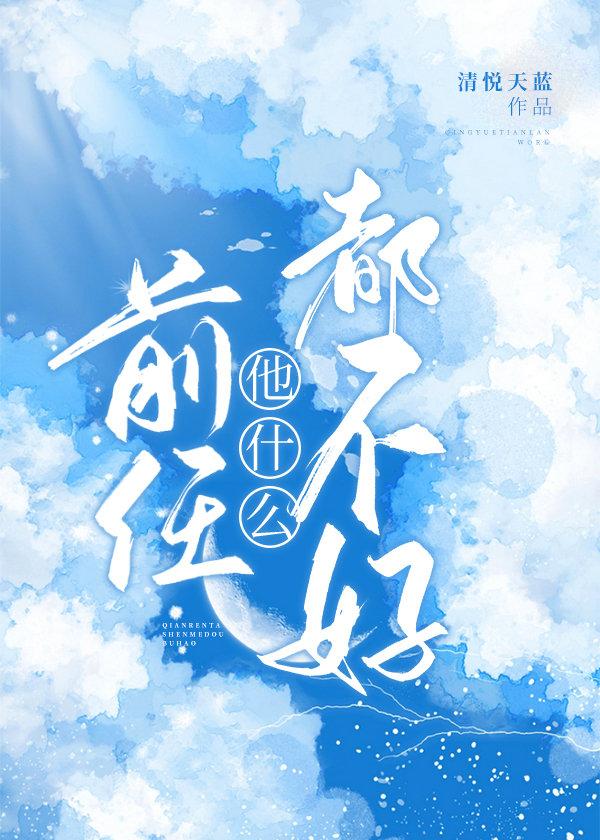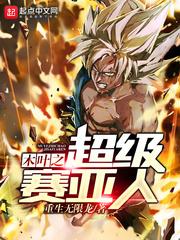69中文网>伟光正老大的秘境探索 > 第163章 不明白(第1页)
第163章 不明白(第1页)
“出淤泥而不染的终归是少数人,大部分人都是淤泥而已。这种话听起来虽然很不好听,但是它是事实。”
“哦?是吗?阁下已经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了吗?哇偶,请允许我惊叹一下。毕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坐而论道一定会令人明智吗?
不,不能了。
因为,“死去的圣人将【清晰】带走了。祂只教会了世人应该对万物都有质疑态度,却未能让世人拥有自知之明。害,自知之明?圣人本以为这是大家都有的,没成想这只是祂,,,”
“你是圣人吗?你不是。那么,你怎么能懂圣人呢?”
“置身处地、感同身受。这是圣人交给我们的立身之本。礼法、是非、阴阳之别皆出自其中。你我都知道,我仅仅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任何其他任何用意。若不用不同的个体来比较不同的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拿相同的东西怎么区别不同的东西?人,绝不相同。善恶亦是如此。”
无聊的辩论呐。
圣人死去后,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人明智起来的辩论了。因为,
“世人喜欢以偏概全,更喜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拿真心对他们,他们呢?不懂的人怎么可能有真心?”
“,,,你的意思是说:我用潭底烂泥与不染莲花为区别,会有人觉得我是在自比莲花,而用烂泥形容他们?不会吧不会吧?世人的想法应该不会如此粗鄙吧?”
“光辉与丑恶是人性的矛盾。你的话,其中用意在他们看来是模糊的。如此一来,,,”
“胡说八道!老夫早已把用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人怎么可能对我的善意视而不见?”
名家善辩,不善解人意。
人意?人?
“丑恶的与光辉的是不同的!你的话在旁人看来,不免有未说出来的暗示。就像是,e”
沉默了许久后。
他缓缓说道:“就像是先贤隐士用菊花自比,先祖君王喜欢用牡丹自比。菊花象征隐士,牡丹象征君王。愚蠢的凡人总喜欢以偏概全,有些人一但听说有人自比牡丹,他们就要说:哎呀,此人好不要脸呢。花中之王岂是此人可以用来,,,”
皱眉,疑惑,打断道:“阁下在胡说些什么呢?世人怎么可能如此不明智?区别与不同他们是能看出来的。”
轻笑,抚掌,解释说:“模糊的东西从来都是不能清晰的。圣人认为这不行,模糊的容易导致扭曲,扭曲后的人不得善终。圣人看见了悬崖边上的我们,祂善、祂好、祂心软了。然后祂来人间教化我们了。之后,我们变成什么样了?不是还是这样吗?只是懂得更多,更擅长模糊是非黑白了罢了。太蠢了,无药可救啊!圣人都救不了啊!!”
自称明智的人是明智的吗?会不会是欺世盗名之徒呢?圣人让世人学会了学习,世人却拿学来的东西去模糊圣人设置下的规矩,因为有利可图。
当事者说着说着热泪盈眶,他的泪水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为了他人。仅仅只是感触良多。
他悲伤了。
一旁的人劝慰道:“阁下说的太绝对了,太悲观了,太险恶了。世人并非无药可救,如果你真的对他们失望了,你可以去看看域外蛮夷嘛,他们才是真正的无药可救。虽然这种话听起来真的很不好听,但是,人是可以从他人的苦难中得到喜悦的。人性本恶,不外如是。”
听到这里。他停止了无意义的伤心,缓了缓后,说:
“蛮夷不知规矩,拿我们去和蛮夷比?这不是拿傻猫与蠢狗比吗?能比出个高低才是笑话,恕我直言,世人本就是无药可救的,只不过,圣人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本质罢了。”
身旁之人对此不置可否,并发出质疑:“本质能改变吗?”
“不能。”他如此说道。
“不能的话,圣人怎么会出来教化我们?”
“,,,”想了想,恍然大悟,“能变的肯定不是本质,看来【无药可救】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揣测罢了。哈哈哈哈”
清晰的绝不模糊。
模糊的从不清晰。
这些只是某一个凡人的妄言罢了,要知道,这个世界可从未与人讲过道理。身处其中,讲道理有什么用呢?
另一处,应该是山谷。
有人交谈。
他们是无聊的,也是愚蠢的。